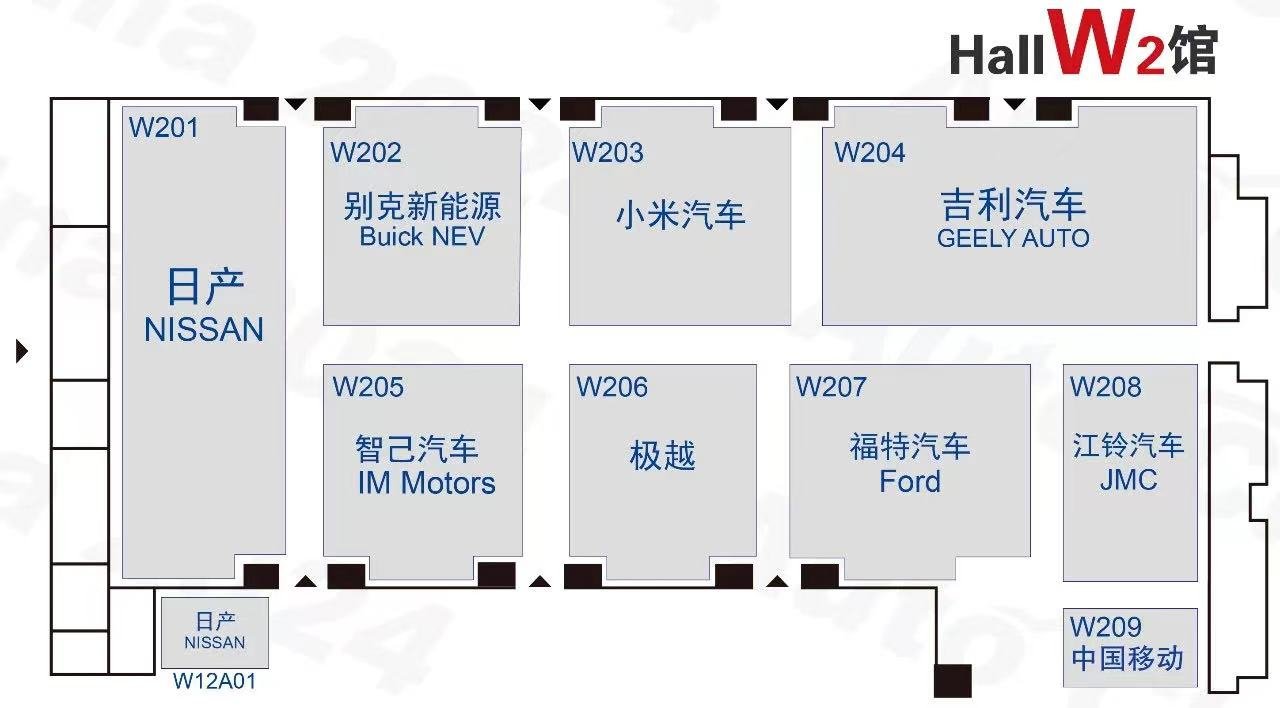导读
受制于新冠疫情的反复与供应链的瓶颈,全球似乎即将进入经济增速放缓、通货膨胀抬升的“滞胀”环境之中,各国政府与央行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对此,学术界关于美国在80年代走出滞胀、开启“大缓和”时代的研究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参考。主流观点归因为:沃尔克时期货币政策目标的转变以及里根政府对工会组织强硬的态度打破了“工资—通胀”螺旋;里根政府采取减税等财政政策促进投资,使得经济重新恢复活力;经济结构的转变以及信息技术的运用改善了库存行为。但需要关注的一个不同的结论是:移民的涌入和中国加入世界分工,才是压低长期通胀的趋势性因素。如果该结论成立,在中国老龄化的趋势下,过往“成功经验”的有效性将接受当下的考验。
摘要
1 滞胀能否被扭转:传统范式与新的挑战
受制于新冠疫情的反复与供应链的瓶颈,全球似乎即将进入经济增速放缓、通货膨胀抬升的“滞胀”环境之中,各国政府与央行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对此,学术界关于美国在80年代走出滞胀、开启“大缓和”时代的研究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参考。在传统框架下,大部分的学术研究认为:沃尔克时期货币政策目标的转变以及里根政府对工会组织强硬的态度打破了“工资—通胀”螺旋;里根政府采取减税等财政政策促进投资,使得经济重新恢复活力。最终在货币政策作用机制的转变、经济结构优化以及外部冲击较弱的共同作用下,美国走出了滞胀,进入产出与增速波动率均较低的“大缓和”时期。但也有一些学术研究对上述观点形成了挑战:人口因素也是“大缓和”背后不可忽视的力量之一。“大缓和”时期美国移民人口增速明显加快,劳动人口占比的提升有助于美国在“大缓和”时期维持较低的通胀水平。而中国加入世界分工,也帮助发达国家长期维持了低利率+低通胀的组合。
2 美国走出1970s“滞胀”的关键:打破“工资—通胀”螺旋,减税释放经济活力
“工资—通胀”螺旋上升是导致美国70年代出现滞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通胀预期产生的原因来说,1960-70年代美联储货币政策对通胀的过度容忍是不容忽视的因素。面对这一情况,沃尔克时代的货币政策与其前任有很大不同,具体体现在:(1)宣布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从短期利率切换至货币供应量,同时将联邦市场基金利率的波动幅度的容忍度扩大至4%;(2)关注实际利率,坚决执行紧缩货币政策以打压通胀;(3)先发制人,将恶性通胀扼杀于萌芽阶段。同时结合里根政府对于工会的强硬态度,最终打破了“工资—通胀”的螺旋式上升。但货币紧缩的代价便是经济进入衰退,因此里根政府采取减税新政以刺激经济增长,释放资本活力。在沃尔克货币政策转向叠加里根新政的组合下,美国最终走出了1970s的滞胀循环。
3 步入“大缓和”时代:是运气好、货币政策优化还是技术进步?
在摆脱“滞胀”的困境后,美国经济进入了一段超过20年的平稳增长期,即“大缓和”时期(The Great Moderation)。这一时期的经济特点是宏观经济的波动性大幅降低。对于“大缓和”的经典解释主要有以下三点:(1)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金融危机以前,原材料价格、自然灾害等外部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相比于70年代时要小,即“运气好”;(2)货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有明显的改善,有助于稳定产出与通货膨胀的波动;(3)经济结构的转变、信息技术的运用改变了生产商的库存行为,降低了经济周期所带来的波动性。除此之外,人口因素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大量研究显示,在储蓄—投资均衡框架下,劳动人口的提升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
4 对当前的启示:低利率、低通胀、低波动时代可能已经过去
当前的经济环境与大缓和时期出现了很大的不同:“运气好”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新冠疫情这一外生冲击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地缘政治紧张加剧、“逆全球化”等因素凸显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信息技术对库存管理的助益大打折扣。更让人值得思考的是,如果 80 年代以来的大缓和或许是人口接力(移民+中国加入分工) 形成的红利,那么中国的老龄化也正在成为发达国家最大的问题,且很难被政策协调真正解决。老龄化真正面貌恰好是通胀的原因,而不是抑制因素。十多年来低利率、低通胀、低波动的环境可能正在被逆转, 寻找更高实际收益率的资产成为所有投资者的挑战。
风险提示:过往历史并不代表未来;学术文献研究并不能直接指导证券投资。
1. 如何走出“胀”
打破“工资—通胀”螺旋
“工资—通胀”螺旋上升是导致美国70年代出现滞胀的主要原因之一:首先,通胀没有在苗头阶段被控制住,并且触发了居民对通胀持续上升的预期;继而劳动力在通胀预期的推动下要求企业提高报酬导致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成本上升一方面会降低全社会产出,另一方面会推动商品价格继续上升,进一步推动通胀/通胀预期上升,形成恶性循环。由此可以看出,美国70年代通胀居高不下,其核心原因在于通胀预期持续被加强。
1.1 控制通胀预期:沃尔克时代的货币政策
就通胀预期产生的原因来说,60-70年代美联储货币政策对通胀的过度容忍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在1979年8月保罗·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前,利率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联邦基金市场利率的波动区间被限制在0.5%(Sumo,2006)。美联储货币政策造成居民通胀预期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其“Stop-Go”的利率调控模式。所谓“Stop-Go”的操作模式,指的是美联储在Go阶段(放松阶段)放松货币政策以刺激就业,通胀率缓慢上行;当公众与美联储都对物价过快上涨感到担忧时,便进入“Stop”阶段(收紧阶段)。Goodfriend(2005)指出,紧缩货币政策的时间窗口非常短,只有当通胀成为主要矛盾时窗口才会打开,而当收益率开始增长时便会关闭;而且由于美联储对经济衰退更为敏感,因此不能充分利用这一窗口,使得“Stop-Go”模式本身就会带来通胀的加剧。
1979年8月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时,面对的最大挑战便是居民并不相信美联储会下定决心治理通胀,这实际上是通胀预期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在1979年9月18日FOMC会议上,美联储以4-3的投票比例将贴现率从10.5%提升至11%。尽管利率提升,但媒体将这一投票比例解读为货币政策将转向宽松的征兆,大宗商品在这次FOMC会议后全线上涨(Lindsey,2005)。

面对这一情况,为了树立美联储的威信、使居民相信美联储对抗通胀的坚决态度,沃尔克时代的货币政策与其前任有很大不同,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979年10月,沃尔克宣布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从短期利率切换至货币供应量,同时将联邦市场基金利率的波动幅度的容忍度扩大至4%。究其原因,Goodfriend (2005)认为:通胀预期的波动率过高,美联储难以跟踪公众的通胀预期以确定合适的名义利率、预测公众的反应,公众同样难以准确辨识美联储的真实意图。Sumo (2006)指出:在原先的货币政策框架下,美联储选择的目标利率与其目标货币供应量之间并不匹配,最终目标利率往往低于目标货币供应量所隐含的利率水平,否则联邦基金市场利率的波动性将超过美联储可承受的范围。Lindsey (2005)总结了12点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增强公众对美联储的信心。
70年代滞胀的出现,以菲利普斯曲线为“镇山之宝”的新古典综合学派饱受质疑,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新自由主义学派应运而生,且有较大影响力。沃尔克提出的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方法与货币主义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亦有助于增强公众对美联储控制通胀的信心(Goodfriend,2005)。
(2)关注实际利率,坚决执行紧缩货币政策以打压通胀。在沃尔克以前,当通胀预期抬升时,美联储名义利率的提升幅度往往小于通胀预期的提升幅度;而沃尔克时期则同时提升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Cralida, 2000)。可以发现,从1980年开始美国的短期实际利率(联邦基金利率 – 通货膨胀率)水平有明显的抬升。除此之外,即便是在1981年7月至1982年底的大衰退期间,美国的短期实际利率(联邦基金利率-通货膨胀率)几乎都处在5%以上。
(3)先发制人,将恶性通胀扼杀于萌芽阶段。80年代早期美国居民的通胀恐慌情绪使沃尔克充分意识到通胀预期失控的危害性,因此即便是在1983年通胀基本控制住的情况下,美联储仍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当通胀预期上行时便收紧货币政策,以免出现实际的恶性通胀。Goodfriend (1993)以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作为工具,发现1983年以后美国仍出现两次通胀预期快速上升的时期,分别出现在1984年和1987年;针对这两次通胀预期的上行,美联储均收紧货币政策,最终并未形成恶性通胀。

1.2 控制工资上涨:震慑工会组织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工会有着很强的势力,工人罢工事件屡见不鲜,涉及1000名以上工人的罢工活动超过400次。工会的过度强势一方面会使得工人的劳动报酬上涨过快,助推通胀上行;另一方面也使得罢工变得“有恃无恐”,进而造成对生产的损害。
罗纳德·里根在就任总统之初便对美国的空中管制员工会(Air Controller Union)工会进行了一次“杀鸡儆猴”式的打压。1981年8月3日,美国空管员工会组织大罢工,希望联邦政府同意提高报酬,并将每周的劳动时间缩短至32小时。这一次罢工对美国国内的运输服务造成极大影响,美国政府将其定义为“危害国土安全”,并勒令罢工参与者在48小时内重新开始工作。然而,8月5日时仍有大量空管员并未返回岗位,里根政府宣布将这11345名非法罢工的空管人员全部罢免,且永远不会再被联邦政府聘用(Beik,2005)。
由于空管员工会在里根竞选总统时曾对其大力支持,因此这次对空管员工会的严厉打击令其他工会组织大为震惊。由于政府在对待工会的态度上明显变得更为强势,美国国内发生罢工的数量在80年代初期快速下降。至1985年,美国每年爆发的罢工次数从1974年的峰值424次大幅下降至54次。(U.S. Census Bureau,2008)

结合紧缩的货币政策与对待工会更为严厉的态度,里根政府与美联储合力打破了“工资—通胀”螺旋的恶性循环,在较短的时间内控制住美国公众对通胀的预期,逐步解决滞胀中“胀”的问题。1980年时,通胀在所有美国人最担心问题的排行榜中高居第二位;到1983年时,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下降至4%以下,恶性通胀基本得到控制;1985年时,只有2%的美国人仍认为通胀是需要担心的问题。

2. 如何走出“滞”
里根新政为经济注入活力
80年代早期,解决经济增长停滞与失业问题主要靠的是财政政策。王剑(2011)认为里根时期的财政政策有三大特征,分别是大规模减税、放松政策管制并降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以及扩大军费开支同时缩减非国防开支。Laffer(2008)认为里根经济政策主要有6大特征:(1)降低税率;(2)消除高通胀并保持美元强势;(3)缩小政府规模;(4)放开能源、金融服务、交通运输等关键领域的管制;(5)扩展自由贸易,拥抱全球化;(6)扩军并试图打赢冷战。从结果来看,里根的财政政策起到了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以失业率和通胀率合成的、反映公众对经济困境感知程度的经济痛苦指数(Cohen,2014)在80年代早期有明显下降。

减税政策是里根经济政策中的核心。里根在上任之初便在1981年通过了《经济复苏税收法案》(Economic Recovery Tax Act of 1981),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从70%下调至50%,资本利得税的税率从28%下调至20%,各税率区间的上下限随通胀指数调整。
其实在里根政府之前,尼克松、福特与卡特时代也曾推出减税政策以刺激经济,但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与此前三届政府有三处显著的不同。(1)里根政府的减税力度空前巨大:以1992年美元不变价衡量,1981年《经济复苏税收法案》通过后两年内实际减税近1800亿美元、四年内减税超过5700亿美元,大幅超过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时期的减税幅度(见图6)。(2)以直接更改税率的方法进行减税:无论是1981年的《经济复苏税收法案》还是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下降至28%,公司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下降至34%),减税的主要实现方式均是降低税率;而此前的减税政策中,除1978年的《收入法案》外(公司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48%降至46%),其他法案均是通过增加税收抵免与抵扣额度实现的。(3)将各税收档位的区间与通胀指数相挂钩,随通胀变化而调整。在1982年以前,美国各档位的税收区间是不与通胀指数挂钩的:当通胀大幅上升时,即使在纳税人的真实收入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仅仅是名义工资的上升也可能使得纳税人适用于更高的边际税率,即税档攀升(bracket creep)现象。税档攀升实际上降低了居民的真实收入。Tempalski(2011)在其研究中指出,70年代高通胀带来的税档攀升使得政府不得不通过减税的方式以维持收入在合意水平。由于税档攀升的存在,尼克松、福特与卡特时代减税法案的效果会随着通胀的上升而减弱。而《经济复苏税收法案》规定税档与通胀相挂钩,其减税效果则明显逐年提升。

美国经济并没有在减税政策推行之初便立刻走出衰退,衰退期一直持续到1982年12月,这可能与减税政策从提出到实际落地的时滞有关。供给学派代表人物、里根的经济顾问亚瑟·拉弗对这一情况似乎早有预料:在《经济复苏税收法案》通过之时,他便提醒里根减税政策落地需要时间,减税实际生效过晚将会导致经济复苏延迟。里根原计划在上任第一年内降低20%的个人所得税率,但1981年美国家庭实际上只享受到1.25%的税收减免,1982 年时也不过是10%。(Laffer,2008)
Laffer(2008)认为减税政策的实施与1983年开始出现经济复苏出现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其原因在于减税政策鼓励风险承担,鼓励企业家精神,同时有助于释放信息技术的增长潜力。
具体来看,减税政策主要通过影响投资行为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减税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亚瑟·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线”——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Laffer,2004)。Roberts(2013)指出,如果一个企业可以接受的回报率是10%,那么在50%税率的环境下,这个企业只有在税前收益率达到20%的情况下才会做出投资;而降低税率有助于提高税后实际回报率,进而增加投资总量。Laffer(2008)认为,减税政策改变了过往投资标的集中于市政债、地产信托等免税项目的投资模式,提高了投资效率;同时资本利得税的降低有助于风险投资资金池的扩大,促进新兴科技领域内小企业的发展。美国小型企业投资委员会主席Brent Rider在1982年国会证词中曾指出:“过去20年中,高科技领域几乎所有的重要新兴公司——如苹果、英特尔、Atari及Data General等——都曾得到过风险投资的支持。”所得税率的下降同样有助于海外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活动,从1983年开始,美国从资本净流出国转变为资本净流入国。

除减税政策外,放松管制政策也是里根财政政策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里根在上任第一天便解除了针对油价与天然气价格相关的管制措施。Crandal(1997)在研究中指出,1978-1995年间天然气、航班、铁路、通讯和卡车行业的价格下降了25%-60%,消费者每年从放松管制中获得的净收益达550亿美元。
3. 走向“大缓和”
在摆脱“滞胀”的困境后,美国经济进入了一段超过20年的平稳增长期,即“大缓和”时期(The Great Moderation)。根据美联储的界定,大缓和时期开始于滞胀之后的1982年中,结束于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末。这一时期的经济特点是宏观经济的波动性大幅降低,Bernanke (2004)指出:相较于80年代初期,“大缓和”时期真实GDP的波动率下降了1/2,通货膨胀率的波动率下降了2/3。

3.1 对“大缓和”的经典解释:弱冲击、货币政策优化、库存管理改善
Bernanke(2004)认为宏观波动降低对经济发展有益,因为宏观波动降低有助于提升市场有效性、降低因预防通胀而导致的资源浪费以及实现更为稳定的就业。至于“大缓和”为什么会出现,学术界认为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原因:
(1)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金融危机以前,原材料价格、自然灾害等外部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相比于70年代时要小,即“运气好”。Stock和Watson(2002)在研究中通过使用随机波动率、VAR等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产出波动率的下降进行归因测算,发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产出波动率下降的贡献为20%-30%,外生冲击较弱以及其他幸运因素对产出波动率下降的贡献约为70%-80%,其中生产力冲击与大宗商品价格冲击较弱的贡献为20-30%,其他幸运因素的贡献为40%-60%;Ahmed(2004)同样通过VAR进行测算,认为产出波动率降低的最主要驱动因素是外生冲击较弱,而通货膨胀波动率下降的主要驱动力则是货币政策的改进。
(2)货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有明显的改善,有助于稳定产出与通货膨胀的波动。Romer(2002)和Friedman(1996)在研究中指出,70年代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表现较沃尔克-格林斯潘时代的表现要更差。Clarida(2000)通过对美联储前瞻性政策反应函数进行估测发现沃尔克-格林斯潘时代的货币政策和前沃尔克时代有较大差异:当通胀预期抬升时,美联储在前沃尔克时代倾向于提升名义利率但降低实际利率;而沃尔克-格林斯潘时代则同时提升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在粘性价格模型下,前沃尔克时期的货币政策使得恶性通胀可能以通胀预期自我实现的形式爆发。Lubik(2004)同样指出,在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下,70年代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会出现多个均衡解,因此在外部冲击下会放大不稳定性。Bernanke(2004)认为货币政策机制的转变具有渗透性,部分货币政策改善所带来的贡献可能被认为是外生冲击或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
(3)经济结构的转变、信息技术的运用改变了生产商的库存行为,降低了经济周期所带来的波动性。Willis(2002)指出,在“大缓和”时期,劳动力供给更具弹性,企业投资所需的融资来源更为稳定,信息技术进步改进原材料与库存管理方式,上述因素共同推动通货膨胀的波动率下行。Kahn(2002)认为信息技术的进步是产出波动率降低的主要原因,其直接表现为信息技术的运用改变了生产商的库存行为:经济产出波动率的降低大部分可通过耐用品产出波动率的降低来解释;同时耐用品需求的波动率并没有同等程度的减小,指向库存行为的变化是推动产出波动率降低的主要原因。

3.2 不容忽视的因素:劳动力的正向冲击
就“大缓和”时代的成因来说,除弱冲击、货币政策、库存管理优化这三大学术界探讨较为充分的因素之外,人口因素同样值得关注。大量研究显示,在储蓄—投资均衡框架下,劳动人口的提升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Goodhart(2017)在研究中指出,劳动年龄人口具有通缩效应,而被抚养人口具有通胀效应:生产具有扩大商品和服务存量的能力,因此具有通缩效应;被抚养者是纯粹的消费者,因此会产生通胀的力量。Lindh(2000)在研究中将生命周期消费行为与威克塞尔通胀积累过程相结合,同样发现净储蓄人口的增加会降低通胀,而退休人口在消耗养老储蓄时会增加通胀。
二战之后,美国迎来了“婴儿潮”一代。受这一人口冲击的影响,从战后到60年代初期,美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始终在下降;而随着“婴儿潮”一代的成长,美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在60年代和70年代逐步上升;而在“大缓和”时期,美国的劳动人口占比基本稳定在66%上下,在2007年时达到最高值67.3%。此外,“大缓和”时期美国移民人口增速明显加快:从1960-1980年间,美国移民人口只增加了约550万人;而在1980-2000年间,美国移民人口的增长超过了1800万人。劳动人口占比的提升有助于美国在“大缓和”时期维持较低的通胀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的作用同样不能忽视。从1990至2007年间,中国劳动人口占比从65.8%上升至73%,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增长超过了2亿人。Goodhart(2020)认为,中国劳动人口的增长给世界贸易体系的可用劳动供给带来了巨大的正向冲击;同时经济自由主义在过去几十年内被广泛接受,国际贸易壁垒降低,增加了全球新增劳动力可以被利用的机会。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金融危机之前,无论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绝对金额和相对占比,其增长速度均明显加快。


4. 对当前的启示
美国80年代初期最终走出滞胀的困境,其成功经验可以从走出“胀”和走出“滞”两个维度进行总结。从走出“胀”的角度来看:美联储在沃尔克的带领下坚决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在增强民众对美联储对抗通胀信心的同时控制住通胀预期,是最终走出恶性通胀的主要原因。从走出“滞”的角度来看,美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与里根政府以大规模减税为核心的财政政策相契合:资本活力得到释放,在电子、信息技术等对能源依赖度较低、且高附加值、高成长的行业中形成有效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
回到当下,从数据表现上看,当前全球的经济形势与70年代滞胀时期有相似之处: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已是市场共识,能源紧缺、供应链受阻的现象在世界多地均有出现,美国劳动力工资快速上升、核心CPI持续上行并逼近1991年以来的新高。
美国在70和80年代对抗通胀的经验表明,中央银行如果一味地重视充分就业而对通胀上行过分容忍的话,会导致中央银行的威信降低、助推通胀预期的上行;而重树央行威信、打破“工资—通胀”螺旋的成本是巨大的,甚至有可能带来经济衰退。因此,在美国通货膨胀率逐步上行的环境下,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在12月15日的议息会议中决定加快Taper节奏,点阵图大幅前移,预计2022年将会加息3次。
回到国内来看,与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不同,中国人民银行在7月和12月先后两次普降存款准备金率。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内并未形成全面通胀的压力,PPI向CPI的传导目前来看并不顺畅,同时在保供稳价的政策下PPI也开始有所回落;另一方面,国内经济数据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放缓特征,走出“滞”更重要。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未来需求企稳回升的情境假设下,通胀向下游传导可能更为顺畅,出现经济企稳反弹+PPI维持高位+CPI回升的组合。

站在长期的视角来看,当前的经济环境与大缓和时期出现了很大的不同:“运气好”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新冠疫情这一外生冲击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地缘政治紧张加剧、“逆全球化”等因素凸显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信息技术对库存管理的助益大打折扣;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均在下行。过去十多年来低利率、低通胀、低波动的环境可能正在逆转。
与美国1970s需求供给共同推升的通胀不同,当前推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集中在供给端:一方面,短期来看新冠疫情的反复对商品生产与运输造成了冲击;另一方面,能源转型背景下对能耗/碳排放的限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的短缺将在长期制约供给。面对上述供给限制,如果仅仅通过政策收紧从而压制需求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更何况需求本身就处于相对疲软的状态,政策限制也十分明显,这与当时沃尔克时刻面临的取舍相似。从历史上看,解决供给瓶颈大多依赖于技术进步,无论是能源方面的技术发展还是制造业生产方面的技术进步: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拉动社会资本进行有效投资,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将释放生产力,从而打破供给限制降低通胀。
从这个角度看,在技术进步真正到来以及大范围应用之前,由于新冠疫情、能源转型以及老龄化共同带来的通胀问题可能很难真正解决,投资者此时更应该关注的是实际回报率而非名义回报率,如何跑赢通胀将可能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所需要面临的问题。
风险提示
过往历史并不代表未来;学术文献研究并不能直接指导证券投资。
 下载格隆汇APP
下载格隆汇APP
 下载诊股宝App
下载诊股宝App
 下载汇路演APP
下载汇路演APP

 社区
社区
 会员
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