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午后,波士顿新闻大厅的摄影记者们为争得一个好机位,相互推推搡搡,文字记者们飞速敲击着键盘,不断更新着消息。
所有人伸长了脖子,等待着联邦检察官安德鲁·莱林,披露美国最大一宗高校招生舞弊案。
西边大陆的蝴蝶扇动翅膀,东边大陆刮起一阵风暴。
很快,风暴横扫了一家A股公司。
步长制药那位新加坡籍老板赵涛,豪掷650万为其千金上斯坦福“走后门”故事,很快家喻户晓。
一拥而上的媒体们,迅速就将“赵家”的发家故事,里里外外全方位扒个精光。
走后门不稀奇,关键是钱的来路。
“赵家”致富,依赖于“国粹”的中医药。在我国,这一领域不仅牵扯到一个庞大“官、学、商”产业链的利益,甚至可以上升到意识形态之争。
话题很敏感。
据米内网数据,2017年,全国医院用药市场约8300亿元,而公立医疗机构中成药总体销售额为2848亿元,占比可观。

来源:米内网
这里面还不包含中药饮片、汤剂及OTC零售市场。
一盒真正见效的抗生素,价格差不多10-20元,而作为“辅助药”的中成药,价格往往是前者的数倍。
每年为此买单的公共财政,让步长制药轻轻松松年入百亿。
作为资本市场上的“中国特色”行业,中医药企业到底值不值得投资,想必是广大投资者非常关注的问题。
对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医疗着眼民生,关乎稳定,历来是国之大计,产业链上的企业,其财报所反映的,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医疗政策的结果,而非原因。
所以要真正回答这个问题,理解中医药公司的投资本质,需要从更广阔的时空结构上寻求答案。
1
步长制药第一桶金的故事里,1993年面世的步长脑心通,扮演了关键角色。
专治脑血栓的步长脑心通,其诞生的时点,正好是我国对药品监管形同虚设的年代。
在当时“承包、承包,一包就灵”的观念下,地方被赋予更多的权力,以便其灵活行事。
无论是药厂的设立审批,还是药品的注册评审,统统下放到省一级。
在地方眼中,所谓灵活,就是怎么有利于地方,就怎么来。
管他药品有效无效,只要能行销全国赚钱交税就行,反正我家老婆孩子不吃。
“道德风险”的巨兽就此出笼。
监管的缺位,让药品市场成为典型的“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
相比西药有确切的化学式,有一定的技术门槛,中医药投入门槛低、风险小、来钱快,成了致富捷径,一时间,父老乡亲齐奔小康,神州大地冒出一大批中小药厂。
在那个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的年代,操盘药厂的老板们,别说什么经典名方,看得懂文言文的都没几个,有的甚至大字不识。
这些所谓的“药”,好一点的可能源自民间传说,夸张一点的或许来自周公托梦。
至于生产工艺,那更是各种脑洞大开,更遑论靶标、毒理、药代、临床。
若追溯目前市面上的各色中医药、甚至“独家品种”,源头就在这里。
步长脑心通,可谓其中典型里的典型。
在百度百科对其发明人赵步长的介绍中,有如下描述:
“赵步长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树木结实,虫子能钻洞,地面坚硬,蚯蚓能疏通。”
“经过多次的实验,赵步长惊奇的发现,某些虫类动物体内含有大量水解蛋白酶,死后身体迅速自溶。于是他确认,重用虫类药物,是清除血栓,改善人体供血不足,攻克中风、冠心病的一条独特有效的捷径。”
1993年7月,纯中药制剂“步长脑心通”通过省级鉴定。
从1993年2月脑心通科研攻关进入关键时期到通过省级鉴定,时间只有不到半年。
其实也不奇怪,据《南方周末》报道,当时一年有一万多种新药过批。
而这些地方“杂牌军”,后来有相当数量在那位被枪决的局长执掌药监,推行“地标”升“国标”期间,通过各种暗箱操作,顺利升级为“国字号”。
郑筱萸的起诉书显示,为让脑心通升“国标”畅通无阻,赵步长向其行贿1万美元。
紧接着11月,脑心通又在布鲁塞尔世界发明博览会上,获得尤里卡金奖,比利时国王亲自授予赵步长军官勋章。
尽管看起来有点像史前时期的微商文案。
但这位科研工作者可谓创造了人类药物研发史上的奇迹。
如今这款年销售量达1.25亿盒的爆款药,包装上标注的主要成分:
地龙(蚯蚓)、全蝎、水蛭,赫然在列。
现代解剖学,对脑血栓的致病机理已十分明确,即:
1、动脉粥样硬化导致血管增厚、管腔狭窄闭塞;
2、血栓。
引起脑局部血流减少或供血中断,脑组织缺血缺氧导致软化坏死出现局灶性神经系统症状。
目前主流的预防治疗方案,首选他汀类药物抑制粥样硬化形成,同时应用阿司匹林等药物,抑制血小板聚集,阻止血栓形成,而对于血管狭窄到一定程度的,需进行支架治疗。
看到这里,也许不少读者已存不小疑惑。
脑心通里的昆虫尸体碎渣,真的能治病救人?
恭喜你,与我国百年前的一位大文豪产生了共鸣。
2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
成年后的鲁迅,在《故乡》中用灵动的笔法,还原了12岁的周樟寿对少年闰土的记忆,成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那时的他,还是位天天期盼着捕鸟、拾贝、刺猹,不愁衣食的周家少爷。
然而仅过了一年,他在京任内阁中书的祖父因牵扯科场舞弊案,被钦定为“斩监侯”下狱,父亲受牵连被革去秀才身份,意志消沉,并从此害了病。
13岁的周樟寿此后四年多,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不断变卖家产为父亲买药。
“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
但这些稀奇古怪的药引,并没有拯救他尚处壮年的父亲。
“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父亲死后,饱尝世态炎凉的周樟寿,开始瞪着怀疑的眼睛审视周遭一切。
作为旧社会“因病返贫”的代表,这也让他失去了读书应试的经济支撑。
不得以才学起了洋务,后远赴东洋,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师从藤野先生。
在当时的国民心中,这叫“将灵魂卖给鬼子”。
父亲的病逝,促使鲁迅探求医学真谛,并希望医治苦难同胞,但他最后弃医从文,因日俄战争时期,目睹一群国人在屠杀另一群国人,还有一群国人“赏鉴这示众的盛举”。
愚蠢且麻木,还有残忍。
被奴性扼制的父老乡亲,让鲁迅觉得悲哀又恐惧,半夜睡不着,翻开的史书又全是“吃人”两个大字。
他的思想发生了重要转折:
“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对好友许寿裳说的一番话更是经典:
“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它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他,拿起笔作为武器,用力透纸背的文字掀开了屠杀背后的血腥,试图用呐喊唤醒愚昧无知的国人。
以上引用文字,出自最能代表鲁迅这一思想的作品:小说集《呐喊》自序。
序中,他用平静缓和的语调写下:
“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事实上,鲁迅对中医的看法,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 那一代信奉和传播“赛先生”的中国知识精英阶层的普遍观点。
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傅斯年、梁漱溟、章太炎、吴昌硕,陈寅格......等等赫赫有名的大师,皆在此列。
概而言之,除了中医界,批判中医、废除中医,几成当时知识界的共识。
要知道,尽管那时政治黑暗,战乱频繁,但北洋、民国时期,是大师辈出的几十年。
那时的知识份子地位高、收入丰。
他们著书立说,站在思想和文化前沿,傲骨铮铮,是真正的精神贵族,领一代风气之先。
别说大小军阀吃闭门羹,就算见了蒋总裁,也敢张口就骂。
北洋、民国时代的政府组织形式,乃典型的上层精英治理模式,知识份子大量从政参政,并延续了千百年来“皇权不下县”的传统。
换言之,知识界的共识,决定了政府的态度。
北洋时期,政府明确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体系外,并采取强势态度否决民间自办中医社团的注册,防止其“结党营私”。
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表示:
“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
“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指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一节,难以照准。”
无论是换多少届总理,还是如走马灯般流动的教育总长,坚定反对中医的立场始终未变。
民国时期,同样延续了北洋政府的政策。
1929年,北伐结束,标榜革命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待中医态度更激进,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制定《规定旧医登记原则》,即“废除中医案”。
将中医归为“旧医”,并要求禁止登报介绍旧医,命令废止旧医学校,禁止成立旧医学校等。
但毕竟只是象征上实现统一的国民政府,对各地军阀势力有所忌惮,在中医团体和中药材出产大省的反对下,民国政客对中医常持两面派立场。
最典型的,莫过于那位一生中至少倒戈过八次的冯玉祥。
曾经,作为“激进”新军阀,大老粗出身的将军,赶过“赛先生”时髦,担任河南督军时,搞过强制老中医上西医培训班,把药王庙改成西医院等”革命”行为。
势如破竹的北伐,让他倒戈北洋集团,加入南京国民政府。
“废医案”出台后,由于直接损害了山东、河北,山西等华北省份药材商利益,而药材又是当时国内第四大商品。
要知道,华北,那是他和阎锡山的地盘。
阎老西顾及税收,公开表态“中医药乃北方命脉,断不可废”。
需要阎老西”协饷”的他,屁股马上又坐到支持中医一方。
但总体上看,民国时期,政府尽管口头上表示认同中医,身体上却很诚实的反对。
直到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中医始终未能获得教育部和卫生部的正式认可。
随着百万雄师过大江,穷苦大众翻身做了主人,中医也在沉沦了几十年后,迎来转折时刻。
3
1948年9月1日的黑海,风平浪静,夏末的空气中已泛起一丝凉意。
几个小时后,一艘航行其间的苏联货轮发生了一场离奇的大火,浓烟中,已在政斗中失势,被蒋介石一脚踢开的冯玉祥将军,不幸窒息罹难。
黑海上那桩历史迷案,阻挡了将军奔向自由解放。
他那位热心办教育,怜惜底层疾苦的第二任夫人死里逃生,回到祖国和人民的怀抱。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作为统战对象的遗孀,夫人就任共和国第一任卫生部长。
但师范专业的她,业务上是外行。
卫生部的日常业务工作,由党组书记、副部长贺诚等早在二十年代就参加革命,戎马一生的技术干部主持。
这些“又红又专”的副部长们,早年分别毕业于北大医学院、成都医专、天津海军军医学校等院校,接受过系统的现代医学训练。
当时的医疗界对中医中药前途有三种结论:
一是完全废止,国人疾病完全依靠西医西药;
二是废医存药,改国药为西药;
三是改进中医中药,使之科学化。
后来的历史表明,新生的人民政府选择了第三种方案。
1950年8月的全国第一次卫生工作会召开后,人民政府定了两大调子:
1、中医科学化;
2、旧有医疗机构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的改造。
作为主管机关,卫生部的工作方针,以贺诚和王斌两位副部长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中医是产生于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历史阶段,因此其理论和技术必然受到当时生产力和人们认识水平的制约。
在生产力取得了发展的新阶段,在社会进步的情况下,中医自然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
中医看病,只不过是给那些贫苦的农民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而已。
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卫生部推行的政策可谓对中医釜底抽薪,主要有三:
1、新的中医不应再继续产生;
2、中医进修现代医学,通过考试获取医师资格;
3、不承认中医经验和理论的独立性。
但如果回到建国时的历史情境,会发现卫生部的政策有些太过“超前”,为事情的转向埋下了伏笔。
首先,当时全国合格的医生还不到2万,与全国需要看病的5亿人口,形成了极大反差。
与此同时,在帝国主义封锁下,国内制药、医械工业也是白纸一张,医疗事业举步维艰。
从残酷战争中走来的党内上层精英,其实对中医能力心知肚明,但当时缺医少药的单薄现实让他们很难将中医抛弃。

来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于是就形成了“明知菩萨不灵,又怕把菩萨给砸了”的尴尬。
其次,由于中医是从“每个人是自己的医生”那种本能医学状态脱胎而来的,长期的中医药文化积淀,使得依靠中医谋生的人数很多。
其中在册的中医师就有80多万人,不在册的不计其数,素质更是参差不齐。
民间就讽刺道:
“现在的医家,只要念过一部汤头歌儿、半本儿药性赋,就称国手。……结果是一个病人请十位先生,脉案准是十样儿,往往真能大差格儿。”
要对这些人进行现代医学进修,再通过考试获取医师资格。
可想而知,这等于砸了很多人的饭碗。
而且在当时文盲率高达80%的情况下,老百姓缺乏起码的卫生科学常识,很难对“中医不科学”产生共鸣。
这意味着“改造旧医”几乎没有群众基础。
政策的“激进”,引发了中医们的群起攻之,怪话满天飞:
“卫生部是西医当权,对中医进行专政。”
“解放后人民翻了身,中医没翻身。”
但中医们的牢骚,在身经百战的老革命面前,只能是背景噪音,真正让形势起了变化的原因,要从财政角度予以解释。
1953年,朝鲜战事停歇,一直怀疑我们不是真马列的老大哥,终于接纳了我们的“一边倒”。
很快,“一五”计划启动。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我国确定的“迅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重点。
纵然老大哥愿意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但仍需要我们提供庞大的财政支出预算。
急于求成的思想遇上计划经济,结果就是国民经济的失衡。
执行“一五”计划头一年,基建投入就增长了107.6%,对轻工业的投入可想而知。
此外,我国还主动承担了“支援世界革命”、“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重任,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组织“枪杆子里出政权”。
很明显,要完成“迅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支援世界革命”两大使命,不便宜。
而要解决钱的问题,无非是“开源节流”。
作为农业国,“开源”就是学苏联剪刀差操作,搞粮食统购统销。
至于“节流”,对象自然就瞄准了教科文卫这些“赔钱货”。
培养现代医学人才,建设制药工业和医械工业,既昂贵,见效还慢。
那么,拔高中医,就成了我国在医疗卫生领域勒紧裤带过日子的“最佳选择”。
但“改造旧医”和“中医科学化”是建国时定下的国策,卫生口的领导干部又是血雨腥风中拼杀过来的老革命,资格老、威望高。
思路的转换,往往伴随着人事更迭。
想要扭转政策走向,只有动用非常手段。
很快,一起偶然事件,被敏锐的高层捕捉到。
1953年3月,一位靠笔杆子起家的干部,调任军委卫生部政治部主任后,到一些直属单位走马观花看了一圈,发现了诸如浪费、医疗事故和工作人员不安心的现象。
马上动手写了份卫生部领导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的报告。
这位原名白子明的干部,曾在三十年代震惊华北局的“湖西肃托”中,为求保全自己,被别人当了枪使,滥捕滥杀300多名干部,几乎摧毁了整个湖西区委。
斗争思想浓厚的他,把一般性质的问题说得危言耸听。
正值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关头,上方立即对此报告做出大段批示,要求严查卫生部工作。
由中央文委组成的检查团,没有发现多少官僚主义的问题,“越俎代庖”的指出了卫生部存在着轻视、限制中医的做法。
抓住这个突破口,180度大转弯发生了。
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批判贺诚、王斌等干部的调门一天比一天高,职务被撸不说,王斌甚至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如果不是战争年代曾救过很多高级干部的命,他们很难熬过往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1955年,改组后的卫生部接连发布《关于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和《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
根据通知要求,任何中医生都可以开单子,任何中医单子都可以抓药,任何中医疗法都可以在公费医疗中报销。
这两个堪称“不管了”的文件,直接造成了后来医疗卫生管理工作的一塌糊涂。
一大批中医”官、学、商“机构成立,各路“丸散膏丹”土药更是大行其道,如今造成大量不良反应的中药注射液,也正是在此时被“发明”。
如今的中医药乱象,最早就要追溯到这里。
4
经典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摩根·弗里曼说:
“一开始你恨他,接着你会慢慢适应它,然后你会离不开它。”
这就是体制化的力量。
体制化是个很奇怪的东西,肌肉记忆就是自身体制化的结果,有件事做习惯了,就会忽略其中的细节,思维形成系统,只剩一个输入输出。
这种体制化最佳样本,正是1954年暴风眼中的卫生部,为表示支持中医,慌忙成立的“体制化力量”——中医司。
这股体制化力量,也在以后的岁月里,不仅保住了中医药的历史地位,还帮自己升了官。
1986年,中医司升格为副部级单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隶属卫生部。
首任局长的表态,很能说明这种体制化的思维方式。
“要想将中医药发扬光大,就要实行中医药自主管理。”
这句话的的潜台词,无非是中医药需要一套游离于主流医学外的“中国特色”标准,既要在政策上享受特权,还不能有个婆婆管。
为实现“自主管理”,1988年,这个副部级单位将中药注册评审职能揽入怀中。
药品的多头管理,并没有带来效率提升,反而成功把水搅浑。
在接下来的10年里,它和下放到省一级的药品注册评审一道,共同开启了属于“步长”们等一大批中医药“科技突破”的黄金年代。
直到98年机构大改革,成立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理顺了监管关系。
中药的监管,才算初步重回地球轨道。
1997年,在纲领性文件《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党和政府明确了新时期卫生工作的指导方针:
“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实现中医药现代化。”
“中医科学化”的思想虽然王者归来,但在实际操作中,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还要看体制的努力,历史的进程。
官僚组织的行为逻辑,就是事权事权,有事才有权,才有官位、待遇,把自己管的一摊子事尽可能铺大,用此“体制化力量”换取官僚组织的“合法性”和自我膨胀。
仔细考察中医药局的行为,恰是如此。
根据中医药局的职能描述,第一条为拟订中医药发展的战略,起草相关法律规章。
关键是第二条:
“承担中医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及临床用药等的监督管理责任。”
但事实证明,中医药局监管浮于表面,深层次问题视而不见。
最典型的,就是别具一格的中医药说明书。
2006年3月,药监局发布《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
“药品说明书应当充分包含药品不良反应信息, 详细注明药品不良反应。”
同年,在药监发布的《中药、天然药物处方药说明书内容书写要求及撰写指导原则》里,又给中医药开了后门。
在中药的使用说明书里,关于不良反应、药物相互作用、临床试验、药理毒理、药代动力学等五个方面都可以以“尚不明确”、“尚无信息”或“不列此项”等方式绕开约束。
有关“不列此项”的情况更直白:
“未按规定进行过临床试验的,可不列此项。”
“毒理研究是指非临床安全性试验结果,应分别列出主要毒理试验结果。未进行相关研究的,可不列此项。”
药监局曾在2017年搜集了市面上1618份中成药的说明书,其中80.2%的说明书显示“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一些厂商更是把“尚不明确”,再度包装成“纯天然”、“植物制剂”、“无毒副作用”,甚至“有病治病,无病健身”等蛊惑人心的广告。
先不说疗效,肝毒性、肾毒性、中药注射液不良反应,受害者还少吗?
相反,在推动中医药产业膨胀上,特别上心不说,还显得颇有铁腕之风。
比如,根据2012年中医药局发布的《三级中医专科医院分等标准和评审核心指标》可知:
三级中医院的中药处方(饮片、中成药、院内制剂)处方数占门诊总处方数的平均比例要超过60%。
不考虑中医院实际情况,而是采取一条线划死的“硬指标”做法。
急切心情,可见一斑。
在新一轮医改进入深水区的背景下,“为所欲为”的中医药,开始撞上另外两大副部级单位的“红线”。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读过君临年初关于药监改革文章的读者,一定对毕井泉之前那个“垂拱而治”的药监局印象深刻。
首任局长按律问斩后,继任者战战兢兢,宁可不为,不可错为。
别说指导行业标准、规范的制定,就连药物评审都能拖则拖。
2015年起,新一届药监班子在毕井泉带领下,密集出台政策,以化学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为改革突破口,鼓励创新为改革方向,对医药行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疫苗案追责,他免职丢官,无数人为此击鼓鸣冤,扼腕叹息。
药监改革,不会遗忘中医药。
如果说化学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是存量改革,对自己的亲儿子下手,大义灭亲。
那么对中医药这种“别人家孩子”开刀,存量利益复杂,增量改革就是阻力最小的方案。
查阅药监法规库,关于“中药、天然药物”的指导原则:
2006-2014年,9年时间,仅出台17项,而2015-2018年,短短4年就出台了23项。
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关于中药新药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根据指导原则,中药新药的疗效评价标准,总体上按照化药的审批标准。
要知道,大样本随机双盲试验,是证明药物有效性的黄金定律。
“实行中医药自主管理”的背后,就是以“自成体系”为借口,逃避双盲试验。
逻辑是个好东西。
你可以说中医药理论自成体系、中医药手段自成体系、甚至中国人身体自成体系。
唯独不能说中医药疗效也自成体系。
疗效只有有效和无效两种可能。
据君临所知,别说FDA临床III期,能通过国内临床III期验证疗效的,中医药一个都没有。
2018年是创新药丰收年,药监局先后批准了48个全新药物上市,其中的10个国产新药,有9个是全球首次批准的新分子。
一方面说明了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成效;
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我国在创新药领域取得的瞩目成就。
与创新药一片欣欣向荣比起来,中药新药无论是申报还是批准,皆一路走低。

来源:药智网
无源之水,必将腐也。
水中那些无法验证疗效的鱼儿们,焉能久存乎?
国家医疗保障局
2018年,新一轮机构改革,压轴挂牌的国家医疗保障局迎来了首位主官。
这位名叫胡静林的干部,在财政部度过了20年的职业生涯,副手岗位上呆了9年,辅佐过四任财长。
历史和人民在等待,等待他和他的团队明确医保局的风格和打法。
很快,这位干部用行动给出了答案。
6月,他将首访地定在福建三明。
地处山区的三明,是个老工业城市,未富先老特征明显,2011年前,三明的医保基金早就收不抵支。
比全国老龄化提前十年左右的三明,顺理成章成为医改“极限生存”的样本。
几年间,三明以“二次议价”和“两票制”为抓手,死抠成本,精打细算的医改模式声名鹊起。
2013年底,胡局长的同事,王保安副部长调研三明,此后三明医改先后4次登上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并在2016年初直接向深改组汇报。
那年起,中医药板块褪去昔日迷人光彩。

中药板块、化药板块、医药行业利润增速对比 | 来源:国家统计局,兴业证券
从98年建立城镇职工医保制度,到03年新农合出台,再到07年城镇居民医保落地。
短短9年,我国从干部到群众,搭建了覆盖人数近13亿的三大医保制度。
尤其是覆盖人数最广的新农合出台后,医保大扩容,A股医药板块也一路高歌猛进。
但医保的第三方支付,全民买单模式,先天具有道德风险。
1、百姓虽享受报销福利,但又缺乏统一协调机制管控药物滥用;
2、各地方有自行加减、增补品种权利,倾向于鼓励地方品种;
3、医院医生有逐利倾向;
如此般,看起来好像无人受损的全民买单,让各方皆大欢喜的薅起医保资金羊毛。
医保支出短期快速膨胀,必然带来医保收入赶不上趟,医保基金支付压力持续增大,出现赤字的地区逐渐增多。
2010年底,以主导低价中标“安徽模式”的孙志刚调任医改办主任为标志。
医保控费,开始成为我国医药政策的主旋律。
对于医疗服务来说,廉价和高水平,构成了一个“既要马儿跑还要吃得少”的悖论。
悖论虽然无法整体打破,但内部空间仍大有可为。
有了地方试点摸石头,改革顶层设计者,很快就抓住了主要矛盾。
体现在医药流通环节,为两票制推行,缩减中间环节;
体现在仿制药领域,是一致性评价,提升仿制药质量,加快进口替代;
体现在中医药方面,即限制辅助用药的使用,减少无效药的使用;
体现在创新药模块,则是加速医保覆盖,以量换价,创新优先。
2018年底,“4+7”带量集采试点推行,断崖式下滑的药企报价,让世人初识整合职能后的医保局强悍战斗力,更展示了其坚定推行医保控费的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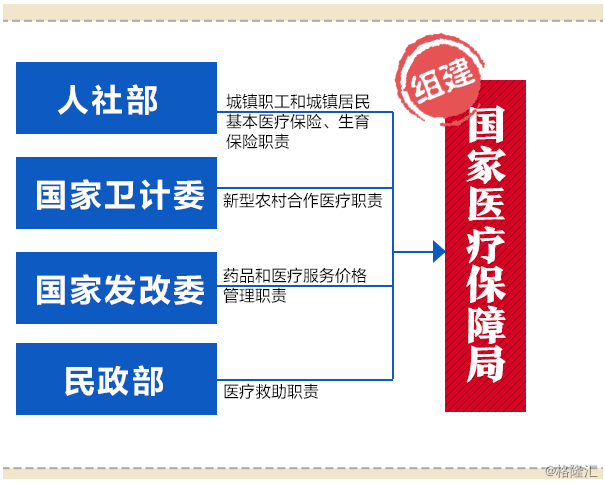
来源:网络
如果说带量集采是无差别轰炸,那么即将出台的辅药目录就是定点爆破。
2018年底,卫健委《关于做好辅助用药临床应用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发布。
文件直指缺乏循证医学证据,但销售金额巨大,临床使用范围广泛,既增加老百姓看病负担,还腐蚀医务人员队伍,又浪费医保基金的各路辅药。
并要求制定全国辅助用药目录,充分评估论证辅药临床价值,按照既能满足临床基本需求又适度从紧的原则,进行严格遴选。
来年2月,焦点访谈以一期《辅助用药,从滥用到规矩用》的专题节目跟进。
节目中,一个骨折病人,用了总共9700多药钱,8200是辅药,其中光是“瓜蒌皮注射液”这个用于“行气除满,开胸除痹”的中药,就花了5080,真正治疗的药其实只花了1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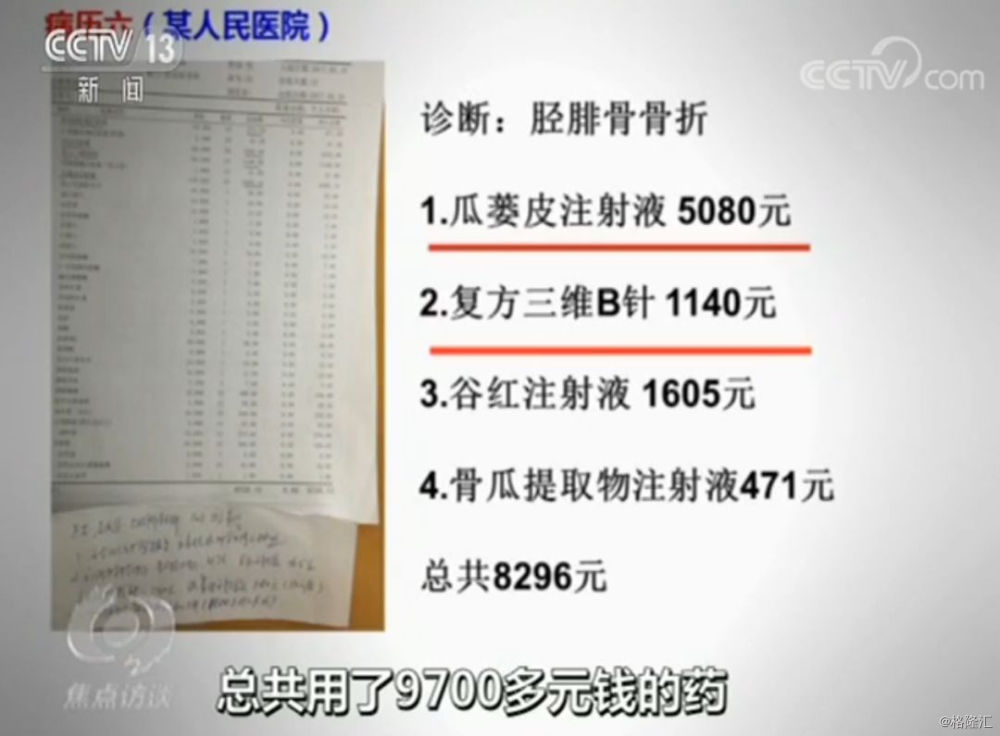
来源:央视
3月两会,胡部长斩钉截铁表示:
“绝不让医保基金成唐僧肉。”
被业内戏谑称为“神药”的辅药,即将迎来共和国之锤的暴击。
尾声
展望未来,对中医药来说,它面前的两大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山头,一位从供给端扎紧了口子,一位从需求端捂紧了钱包。
负面的政策前景,是整个中医药板块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
形势比人强,转型迫在眉睫。
中医药企业要怎么转,屠呦呦发现抗疟有效化合物——青蒿素的故事,就是明摆的例子。
从经典古方中找到灵感的屠呦呦,用鼠疟模型不断筛选尝试,最终发现用沸点35℃的乙醚,才能提取稳定的青蒿素,并用严谨的试验数据证明了对疟疾有稳定的抑制作用。
但到目前为止,君临没有看到任何一家中医药企业,下决心转型到用现代医学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医药。
反而试图钻政策漏洞、公关上下疏通,甚至搬出“文化传承”的大棒,逆潮流而动。
鉴于此,我们认为应中长期看空中医药板块,尤其是中药注射液、中药口服剂收入占比高者。
君临在写作此文,翻阅史料的过程中,由衷敬佩卫生口老一辈专家的远见卓识,抱着理解并同情的态度,叹息时代的风云变幻,领导人的无奈选择。
老革命们否定中医“空对空”的诊断方式,但从没有否定中医药有价值部分,更没有否定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他们力推的政策,本质上无非是:
中医应该成为现代医学研究的对象,而非现代医学研究的指导。
复盘青蒿素的故事,其实就可以看出,古代的杏林名医们,千百年来用不计其数的人体试验,粗糙的完成了现代药物研发的第一步——海量筛选先导化合物的工作。
继承和发扬,不正是中医科学化大有可为之处么。
我们在无谓的争吵和对抗中,多谈了主义,少研究了问题,兜兜转转几十年,才又回到当初的起点。
本文史料部分参考资料
1、《中国中医药50年》 王致谱
2、《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
3、《贺诚传》 冯彩章,李葆定
4、《中医研究》2005年01期:从中医进修到西医学习中医 张效霞、王振国
5、《健康报》1954年10月1日:周泽昭代表的发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的发言
6、《挽救中医》 吕嘉戈
7、《彭瑞骢访谈录》 彭瑞骢
8、《财经》总第522期:如果自己都改不好,何谈更大的改革?
9、《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
10、《建国初期的中医进修(1949—1955)》毕小丽
11、《新中国经济史》 苏星
12、《八次危机》 温铁军
 下载格隆汇APP
下载格隆汇APP
 下载诊股宝App
下载诊股宝App
 下载汇路演APP
下载汇路演APP

 社区
社区
 会员
会员



